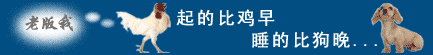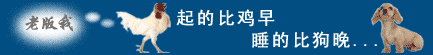放眼当下的中国电视界,可以说是一个娱乐功能空前强化的时期,各电视媒体最为火爆的节目基本上都是娱乐节目。这类节目的大量涌现,应该说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要求。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使人们休闲娱乐的渴望日渐强烈,电视作为大众接触最广的媒体,无疑应当满足人们的这种渴望,娱乐节目也就自然成为电视节目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收视率无疑是指导节目策划和制作的重要指标,但它决不是唯一的标准。根据市场需求,制作、播出一些娱乐节目本来无可厚非,问题是不能“一窝风”,更不能“娱乐至死”。因为过度娱乐化,会遮蔽电视文化的认知、教育和审美功能。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解读收视率的内涵,片面强调用收视率作为评判节目的唯一指标,必然产生某些非理性的做法。
随着电视节目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重视观众需求,关注商家需要,谋求尽可能高的收视率,已经成为媒体经营的着力点。市场机制增强在推动电视业发展的同时,也引来“唯收视率论”的暗流,使得娱乐低俗化现象随之出现。
当前,电视娱乐节目虽然渐成规模,但由于缺乏文化内涵和创新能力,使其渐渐陷入同质化困境。近年来,在商业利益驱使下,一些媒体在价值导向上产生飘移,不再甘于只做现实的“镜子”,还当反映花边新闻的“哈哈镜”。报纸上、网络上的社会新闻经常语出惊人,“芙蓉姐姐”、“虐猫事件”层出不穷;电视上,一些娱乐节目不断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一些在国外饱受争议和棒喝的节目,竟被改头换面地引进和包装。面对种种怪状,中国电视业到了当头棒喝的时候了。
一、为人诟病的种种低俗表现
娱乐低俗之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媒市场化、娱乐化勃兴之后出现的异变现象,主要是指大众传媒在传播活动中放松对自身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片面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使其传播内容格调低俗,品位低下。传媒低俗化在电视媒体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娱乐节目低俗化。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性”为佐料,插科打诨。一些娱乐、综艺节目经常用荤段子、暧昧字眼和暴露镜头来招徕观众。譬如,某娱乐频道2003年曾推出一档气象播报节目,由星姐亚军作主持,只见她身着艳装,躺在沙发里,双脚搭在靠背上“秀”美腿,开讲前还要大跳扭臂舞,在全国引发一场关于“色情报天气”的争论。
其二,暴露残忍,欣赏丑恶。近年来流行的某些“真人秀”节目,掺杂一些以残忍、卑鄙、博彩为看点的情节,刻意暴露人性弱点和阴暗面,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
其三,大兴窥私,挖掘隐情。一些娱乐谈话节目常在明星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出一些隐私问题,让明星们当场现形,尴尬不已,这已经成为一些娱乐节目的拿手好戏。
其四,疯狂“恶搞”,愚弄观众。在一些娱乐节目中,把吃虫子、蚯蚓等内容作为参加者的比赛内容,以“向嘉宾泼馊水”、“食物中偷放兔子屎”等方式来挑战人类感官。
其五,奇装异服,言语无忌。一些主持人不注意内在修养,而是想方设法通过怪异的外形设计来刺激观众。有的男主持言行异化,性别错位;有的女主持穿戴暴露,嗲声嗲气,粗口、卖弄、撒娇、索吻,无所不用。
其六,颠覆传统,演绎龌龊。一些欲借电视迅速蹿红的人,不知廉耻地披露“丑闻”,忸怩作态,以此拉升人气,与节目合谋“双赢”;有的节目以演绎龌龊为能事,专门调选社会畸形现象进行所谓“情景再现”。
其七,高额大奖,刺激暴富。某些娱乐节目,把普通观众装扮成主角,以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梦想”为诱饵,让普通大众投身其中,乐此不疲。这些高额大奖,在增强节目刺激性的同时,也宣扬了“暴富”思想,对社会上的浮躁心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目前,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歌方面的重视,呼吁抵制低俗之风的呼声不绝于耳。2004年5月11日,国家广电总局颁发了《广播影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开始全面实施净化电视荧屏的“四大工程”:(1)“防护工程”,坚决删除节目中与健康生活方式不相容的情节、画面和语言;(2)“净化工程”,坚决制止色情和性为“噱头”、“卖点”等格调不高的影视节目;(3)“建设工程”,在省级和副省级城市电视台逐渐开办少儿频道;(4)“督察工程”,实时监控,“该停播的节目坚决停播,该停办的栏目坚决停办”。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
通知中还规定,坚决纠正节目主持人在着装、发型、语言以及整体风格方面的低俗媚俗现象。要求节目主持人在整体风格上要充分考虑全社会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欣赏习惯、审美情趣,做到高雅、端庄、稳重、大方,不能因过分突出个性风格、个人品位而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不能为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而迎合低级趣味。规定主持人不宜穿着过分暴露和样式怪异的服装,避免佩戴带有明显不良含义标志图案的服饰。主持人的发型不宜古怪夸张,不宜将头发染成五颜六色;不要模仿不雅的主持风格,不要一味追求不符合广大观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审美情趣的极端个性化的主持方式,更不要为迎合少数观众的猎奇心理、畸形心态而使用极尽夸张怪诞的言行与表情。除特殊需要外,主持人必须使用普通话。
人格发展理论研究表明,无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人的一生都存在人格发展的任务。即人的社会化进程将伴随其一生。在社会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要想使大众尽快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明辨荣辱,除了学校和社会机构教育之外,还必须通过大众媒体来完成先进理念的传播。
但是,与此同时,传媒商业化对社会带来的种种副作用也日渐显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与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曾提出:“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于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1]这无疑是对文化商品化弊端的真知灼见。面对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各种理念的纷扰,一些电视业者迷失了方向,忘却了责任,甚至让金钱冲昏了头脑,这是造成传媒低俗化的症结所在。
二、唯收视率造成的种种弊害
片面强调提高收视率,必然引导节目趋向大众化而非专业化,大众化的结果便是频道的综合与雷同,最终导致千台一面、资源浪费、恶性竞争。也就是说,随着新媒体出现和境外媒体抢滩大陆,电视市场的竞争日渐白热化。电视为了自身生存发展,开创了一些新颖独特的节目形态,取得了可观的收视回报,这对媒体而言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一些媒体盲目跟风,片面追求收视率而降低节目品位,放宽广告审核要求,滥播一些恶俗节目甚至虚假广告,严重背离了大众媒体文化传播和审美功能,损害了电视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片面追求收视率导致了诸多负面影响:误导社会舆论,恶化媒体环境,降低文化认知,导致资源浪费……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我国电视业的健康发展,还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部分媒体对收视率数据的简单理解和非理性使用,还导致电视节目出现同质化倾向。传播学认为:作为一个群体概念,受众均有从众心态。如果片面追求收视率,媒体的议程设置同受众的从众心态相结合就会产生强大的蛊惑力,很容易误导观众。如果对那些貌似大众化实则低俗化的节目过分吹捧,在高收视率的幻影之下,观众往往会盲目听信,其结果会引起更大的社会负面效应。
1、导致电视节目同质化,致使资源浪费和创造力减弱
商业化本身所固有的世俗化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催化大众传媒的低劣化。内地电视传媒目前最严重的弊病在于节目“克隆”现象的泛滥。一是对境外节目的“克隆”,二是内地各媒体之间的“克隆”,这一方面缘于内地电视机构的特殊管理体制,各电视台之间的竞争不十分明晰,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内地传媒原创意识与知识产权意识的淡薄。一些电视台在节目定位上一味迎合大众的口味,置观众于最简单的搞笑娱乐层面,照搬港台模式,节目既 “闹”又“乱”,就是把商业利润作为直接目标的体现。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尖锐地指出:“在50年代,当电视作为一种新现象问世时,电视关注的是文化品位,追求有文化意义的产品并培养公众的文化趣味;可是到了90年代,电视极尽媚俗之能事来迎合公众,从脱口秀到生活纪实片再到各种赤裸裸的节目,最终不过是满足人们的偷窥癖和暴露癖。”[2]电视何以从文化和交流的传播手段,沦落为一种典型的商业操作行为?布尔迪厄给出的结论是,这一切都受制于收视率,而收视率又是追求商业逻辑的必然结果。
目前,在使用收视率方面存在两大误区。一是把收视率绝对化,唯收视率“马首是瞻”。追求收视率并没有错,但不能单纯追求收视率,收视率只是电视节目评价体系中的一个指标,不能把它绝对化。二是有些人主观地认为,要得到高收视率,节目一定要低俗、打“擦边球”。其实,高收视率和庸俗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虽然有些低俗的东西可以带来收视率,短期内可能会获益,但有损电视台的形象,有损于媒体的品牌效应,这种饮鸠止渴的短视行为,使最终受损的还是传播那些东西的媒体。
2、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倾向容易滋长社会的浮躁情绪
我们知道,受众使用媒体主要有以下五种动机:(1)获取所期望的信息;(2)延续业已养成的接触媒体的习惯;(3)为了休息或者寻求刺激;(4)逃避烦闷或无聊;(5)陪伴,避免寂寞[3]。从中可以发现:寻求刺激也好,逃避烦闷也罢,都离不开娱乐。于是有人主张电视就是娱乐,娱乐可以带来一切。而当娱乐成为全部目的之后,电视就开始失去它的文化价值。我们常常被一些MTV和广告片中浮华零乱的画面搞得心神不宁,对一些尽显珠光宝气的电视剧产生厌倦。可见,单纯形式化的娱乐,由于缺少必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不仅会丧失审美价值,最终也会因丧失娱乐功能而成为荧屏垃圾。
3、电视暴力镜头容易诱发犯罪
电视暴力效果的研究由来已久,主要担忧电视暴力可能带来消极影响。大量研究支持了刺激暴行的假说——看电视暴力将增加实际的侵犯行为。一个是模仿假说:认为人们从电视上学到了侵犯行为,然后再到现实社会中去模仿;另外一个是免除抑制说:认为电视降低了人们对侵犯他人行为的抑制。这可能暗示一种规范,即暴力是一种与他人交往时可以采用的方式。[4]
凶杀、色情等感官刺激的画面很容易吸引观众,但这种节目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早有定论。传播学者巴伦·李维斯和克里夫·纳斯在十年中完成35项试验后得出一条重要结论:媒体等同真实生活。[5] 1968年,受美国总统指令成立的“暴力产生原因及对策全国委员会”,其研究报告表明:“电视上的暴力镜头与现实生活中的暴力行为有关,是造成暴力行为的社会因素之一。一个人如果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暴力行为,他会误认为现实世界也充满暴力,电视上的暴力镜头会造成一种引起暴力行为的环境气氛、态度及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人们是像对待真人真事一样对待电脑、电视和新媒体的”。[6]这说明,电视媒体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的窗口。如果电视节目中大肆展现低俗内容,势必会使一部分观众特别是未成年人认为其生活的真实世界也同样没有人情、道德沦丧,充满冷漠、自私与残酷竞争,而无助于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稳定和维系。电视媒体不该为自身经济利益而置社会公共利益于不顾,这本身也违背了媒体的公益性和道德操守。
其实,收视率具有两面性。尽管其不当使用会带来种种弊害,但它并非一无是处,是所谓“万恶之源”。因为收视率毕竟使节目有了一把衡量的基本尺度,为节目综合评价提供了重要的测量指标。我们应当理性看待收视率,既不过分强调其正面作用,又不过分夸大其负面作用。
三、绿色收视率出台背景及其基本理念
众所周知,节目评估是电视媒体进行节目质量监督和考评的一项管理机制。一般是运用数理统计和科学测量的方法,按照公认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所播出的节目从选题、意义、结构、语言、手法、效果等各个方面作出评定和估算,以正确把握节目的质量水平,提出改进方向。开展节目评估是进行栏目评估和频道评估的重要基础,对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即媒体影响力)进行评估则是节目评估功能的延伸。
节目评估的对象主要针对播后节目,如果评估指标能够被行业认可,也可以用来进行“播中监测”和“播前预估”。节目评估体系由受众调查系统、受众反馈系统和专家评价系统三部分构成,三部分各乘以相应的加权系数,便可以得出对一档节目较为公平合理的评价。就我所知,目前各电视媒体的收视率数据主要来自央视?索福瑞和AC??尼尔森两家公司,少数单位委托城调机构来调查。可以说,调查公司提供的数据质量直接影响着这些媒体节目评估的结果。当前,我国电视节目评估指标在数据采信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样本量偏少,导致调查数据的精确性不高;二是普遍缺少农村人口样本调查,导致定性分析不准;三是采信标准不统一,使数据缺乏可比性和公正性;四是有主调查造成数据先天性不客观。
出于调查成本的考虑,目前各调查公司在主要城市的样本量一般不超过300户。这个样本量在95%的置信度下,允许误差范围较大,我认为,当样本量扩大到700户时,误差范围缩小到±0.02以内,其调查数据才具有统计学意义。如果各家公司提供的调查数据精确度都不高,可比性、公正性自然也就成了问题。
在节目评估管理者眼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数据采集和计算没有规范统一的标准,数据产生的透明度不高。国外媒体主要采用购买调查机构提供数据的方式(无主调查),而非自己出资为自己做数据调查(有主调查),而国内尚缺乏纯第三方机构独立运作提供的调查数据,单纯由媒体出资委托公司调查这一做法的公正性必然会受到质疑。国外是批评家引导大众收视取向,进而影响收视率,而国内是不科学的样本决定了收视率,进而影响广告商的投放意向,直接或间接裁定了节目生死。由此看来,国内的媒体调查目前确实存在精确性、可比性和公正性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在彻底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下,调查机构提供分析报告和改进意见才有实际价值。[7]
当商业的法则进入到文化领域,收视率控制了节目生产,从业人员只重视广告收益,节目生产被简化为“成本-效益”的时候,低俗化就会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说到底就是对收视率导向的一种误读,是只重经济效益而忽视文化属性的恶果,但是面对电视节目平庸化、同质化、低俗化的现状,我们不是无能为力,而是可以从根源上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收视率所代表的市场力量在电视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它已成为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我国电视产业化的必要动力。收视率的意义,是给广告主与广告商作为其广告支出的参考,是电视台争取广告商付出广告费的标准,但电视台若以此作为衡量节目好坏的唯一标尺,就会犯逻辑错误。因为收视率只是一个表象参数,它无法对节目的个性化程度和观众的喜爱状况提供参考。收视调查无法也不允许为不同的节目设定一一对应的标准,只能把所有节目提到“同一尺度”,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其结果必然有失公允。
近年来,在所谓“商业语境”下,出于竞争压力和对经济利益的追逐,部分媒体不惜以降低节目品质、品位,迎合受众的方式来提高收视率,电视媒体的喉舌功能和导向作用无形中受到弱化,媒体的双重属性要求电视台必须协调喉舌功能和产业功能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重要时期,2005年底,中央电视台提出绿色收视率这一创新理念。它以高收视为基础,以高品质为核心,弥补了以往单一收视率指标的不足,为加强电视节目评估体系的科学化和可操作性提供了依据。绿色收视率注重收视率,但又不惟收视率;主张确保国家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充分保证和体现节目的思想性与导向性,倡导人文关怀和理性思考、塑造高雅的审美情趣、弘扬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绿色收视率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不论传媒生态发生怎样变化,主流媒体都要坚持用健康、高品位的节目打造高收视率,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中央电视台通过绿色收视率表明自己在“倡导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上的责任意识,体现了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公益特征,以及塑造国家大台权威公正形象的信心。
四、以绿色收视率引领电视创新之路
中央电视台提出绿色收视率这一理念,就是用“绿色”体现导向性与思想性,体现品位与责任。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实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对绿色收视率的打造,媒体的双重属性将会得到充分体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以协调发展,及时改变近年来某些媒体为追求经济效益导致导向性弱化的倾向。
目前,中央电视台已经实施节目末位淘汰制。这个“末位淘汰制”决不是只看收视率一个指标,而是通过建立科学的节目分类体系,对影响节目质量的元素进行全面排查,确立以客观评价、主观评价和成本评价等三项指标作为栏目评价的基本指标;再通过对三项指标分别进行权重修正,最终形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简称“三项指标,一把尺子”。
客观评价指标是指以收视率为基础,兼顾频道、时段、栏目类别等因素后获得的栏目收视表现的量化值;主观评价指标是综合专家、领导对栏目评议的量化值;成本评价指标是栏目投入产出状况的量化值。综合评价指标是指统筹考虑栏目客观评价、主观评价、成本评价三项指标之和而形成的节目传播效果的综合量化值。
绿色收视率为解决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找到了一把金钥匙。电视媒体与其他媒体相比,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才能进入良性循环,财力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节目制作的精良程度。没有精良的节目,就很难保证绿色收视率的稳固,电视媒体的“喉舌”作用也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所以,绿色收视率本身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互为表里的一个结合点。
传统经典文化与电视结合,这既是对传统经典文化的复制,也是一种再造。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曾经指出:“有一种与所复制性的东西相对的存在,这就是艺术品的氛围,即艺术作品在其中被创造并且对之诉说的、规定了艺术品的功能和意义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情境。一旦艺术品脱离了它自己的那个不能再重复和不能再挽回的历史时刻,它‘原初’的真实就被弯曲了,或(被精心地)修正了:它获得了另一种历史情境。借助于新的工具和技法,借助于新的感受和思维形式,原初的作品现在也许就会被阐释、编排和‘翻译’,从而变得更丰富、更复杂、更精巧、更有意味。”[8]
今天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电视制作手段大大提高,由前期制作需要的灯光舞美到后期编辑的非线性技术,电视本身的技术手段已经能够承载和再现以往的多种艺术形式。传统的经典也好,现代艺术也罢,都能够通过电视给予观众感官上的延伸。比如,不少栏目在探索全新的电视体裁和表现形式时,打破了传统漫画的平面局限,有效地结合现代电脑绘图技术,加强电视化的技术和艺术表现手段,用动漫手法进行了重新诠释,给传统漫画注入了新的活力,已经演绎成符合当今收视习惯的一种新的文化视听形式。
应该说,电视从业者当今正处在一个电视发展的黄金时期,创作者的想象力已经很难被技术手段所束缚,其创造力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同时,各种经典文化又提供着无尽的创作源泉。只要从业者坚持与时俱进,把最新最好的技术应用到节目创作中去,就能够实现提升节目审美价值的目标。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着重指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促进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共同精神追求。”因此,在目前商业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矛盾初露端倪之时,有必要从媒体属性和媒体职责出发,用绿色收视率理念指导电视节目,也就是在坚持用高品位来打造电视节目的内涵,引领中国电视走上一条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之路。
(本文系作者根据在“首届中国电视批评高端论坛”上的演说整理成文)
注释:
[1]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前言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第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 参见梅尔文·德弗勒等著:《大众传播通论》425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4] 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302页,华夏2000年版。
[5] [美] 巴伦·李维斯、克里夫·纳斯:《媒体等同》“译者的话”第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 [美] 巴伦·李维斯、克里夫·纳斯:《媒体等同》封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 参见张君昌:《节目评估的概念及其置信度》,载视网联《传媒博客》2006年7月10日。
[8] [美]马尔库塞:《作为现实形式的艺术》第192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来源:传播学论坛 (DVOL本文转自:中国DV传媒 http://www.dvol.cn)